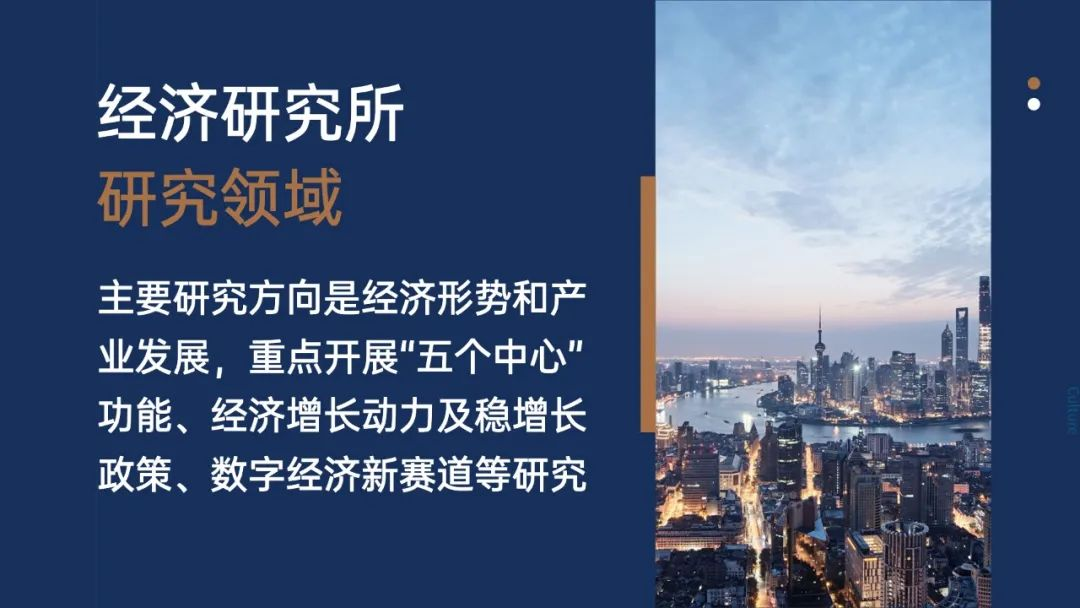美国制造业回流动向及对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启示
作者
马海倩,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,正高级经济师
朱春临,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经济研究所
汪曾涛,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经济研究所
邹 俊,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经济研究所
卢 溪,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经济研究所
张亮靓,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经济研究所
核心观点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,从奥巴马政府“再工业化”到特朗普政府“美国优先”,再到拜登政府“供应链韧性”战略,美国不断加码推动制造业回流,对全球产业链格局带来巨大扰动。对金融危机前(2000-2009年)后(2010-2021年)美国制造业重点经济指标对比分析发现,美国制造业回流效果已初步显现,制造业增加值小幅加速提升,危机前后平均增速分别为1.6%、1.8%;制造业就业人数“V形”由降转升,从危机前减少580.5万人到危机后增加100多万人;制造业私人投资、货物贸易出口增速提高,危机前后平均增速分别为1.6%、4.4%及4.4%、5.3%。
美国制造业回流呈现以下特征:从回流行业看,电动汽车产业链、半导体产业链、战略性关键矿产等领域回流标志性项目多,对我国这些关键行业领域发展的迫切性提出警示;从回流来源地看,美国制造业回流主要来自于亚洲,中国是第一来源国,从中国回岸的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占报告来源地总岗位数的5成以上,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将造成直接影响;从回流目的地看,美国正在推动形成“本土回流+近岸回流+友岸回流”格局,本土回流主要流向美国人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南部和中西部,近岸回流主要流向墨西哥和加拿大,友岸回流在亚太地区主要流向越南、印度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国家,这一方面扰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布局,另一方面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主流供应链之外;从回流驱动因素看,政府激励、供应链风险、生态系统协同等非财务成本因素的影响力在上升,对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提出挑战。
对上海发展制造业问题的启示与再思考:保持制造业总体稳定、稳中有升,对当前稳固疫后复苏基础以及中长期积蓄内生功能至关重要。启示之一:制造业仍应作为上海统筹谋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项。稳增长需要工业的边际增长效用,必要的工业增速对稳增长的边际作用不可小觑。“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5%”,仍应作为导向性的目标,以期形成共识,尽力而为、组合发力。启示之二:上海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和优势。一方面,智能制造、工业机器人等在重构生产流程和组织模式等同时,也在重新定义制造业传统的内涵。另一方面,那些生产高技术含量、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制造企业,通常能够以较高产出覆盖较高成本,其在投资决策中,会给予区域创新能力、人才获取难易、市场成熟程度、专业服务水平等更高的权重,而这些正是上海的长板优势。上海发展制造业关键在于研发、人才、市场、服务等优势的整合释放。启示之三:上海应重点发展高生产效率、高定价能力、高服务融合的制造业。以智能制造提高劳动生产率、以绿色制造提高“碳生产率”的制造业,从而用高效率获取高利润;以高研发投入、高技术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,在市场上具有较强“垄断性”特征和品牌价值的制造业,从而用高产出覆盖高成本;能够承载研发成果转化、生产性服务赋能的制造业,从而用高融合催化制造服务联动升级。启示之四:上海新一轮制造业发展应走出全新的路径模式。从注重相对成本转向注重综合效率,系统构建制造业友好型发展环境;在增强根植性、形成生态上持续下功夫,瞄准目标、久久为功;放在全国大格局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中发挥比较优势,联动区域延伸拓展上海制造业发展空间;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,在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发挥好上海专业服务的赋能作用。
研究领域